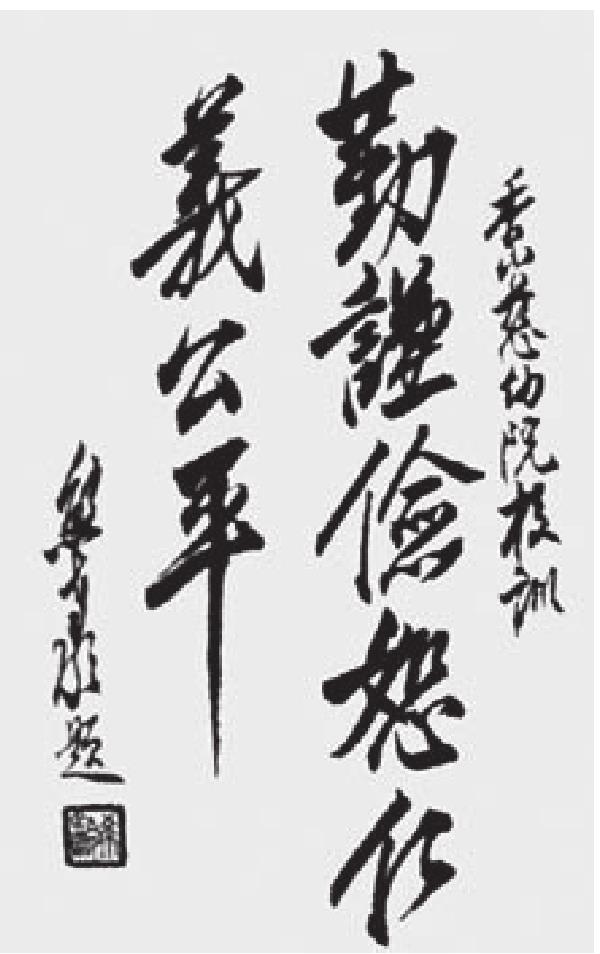一
说实话,我是冲着沈从文而去凤凰的,但是没想到熊希龄却给了我最大的震惊与感动。
熊希龄的家——现在的“熊希龄故居”,在凤凰城北文星街内的一条陋巷中:一座砖木结构的民居,一个不大的院落。居共四间,一间作堂屋;最东边一间是橱房,里面一口柴灶,一口水缸,一副水桶,还有几件农具,其他别无长物;西边两间是卧房,最里面的一间,据说当年熊希龄与朱其慧女士完婚回乡时就曾居于此,内有花板床一张,还有几件普通橱柜木箱之类。导游解说,我们看到的这一切,除了一些对联与展览的图片外,其他都与当年无多大异。
在凤凰城里鳞次栉比的高楼重檐中,“熊希龄故居”实在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
这不能不让我非常震惊,又非常感动!要知道,“熊希龄是个什么人呵!?”
——当导游说“下一个景点是‘熊希龄故居’”时,我们一行中有人脱口而出的便正是这样问道。
“熊希龄是什么人呵?”的确,对于一般人来说,熊希龄这个名字有点陌生。

朴素的熊希龄故居
“这是凤凰出过的最大的官,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导游说。
“哦!那倒要去看看!总理的府上一定很豪华吧?”
“一会儿去看了就知道了!”
……
凭以前对熊希龄的了解和导游的这话,我对于这位内阁总理的府上的朴素多少还是有了一点心理准备,但是竟会是这等模样,无论如何还是大大出乎我意料的!
我第一次知道熊希龄这个名字实属偶然。那是十多年前,我的一个出身于民国官宦之家的朋友,家里存有不少祖辈遗留下来的旧信札,他想搞清楚哪些有保存价值,哪些可以处理掉,便让我帮着看看。那是些很老的信札,纸已又黄又脆了,字迹也已褪色,有的已十分模糊,但是其中一封署名“熊希龄”的信,一下子让我的眼睛一亮,因为那字写得真是漂亮!虽然我当时孤陋寡闻得并不知道这“熊希龄”是何许人,但我还是让他好好保存这通信札。从此以后,我也开始有意无意地关注起这个名字了。
当然,我对于熊希龄的兴趣并不在他曾经亨通的官运,以及他曾拥有的各种吓人的头衔上。清末民初的中国,真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政坛更是像走马灯一般,这造就了太多太多的吓人头衔,而顶着这些吓人头衔的人,其中的庸常者其庸常的一生实际上并不曾因为这些头衔的吓人而有丝毫的改变,当然也不能改变他们被历史淹没的命运。我对熊希龄感兴趣的是,几乎是主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为什么反而终没被历史的烟尘所淹没?
我是个俗人,首先想到的是他的一段风流韵事。
的确,风流韵事(现如今多改称其为绯闻了),是个可让人“流芳百世”的好东西——当其时也,它可以造就新闻,可以吸人眼球,可以将主人炒成社会焦点;而今天的社会焦点,往往便是明天的历史事件呵。所以,君不见在如今这样一个炒作的时代,许多明星和非明星,实在没有炒作的资本了,便都不约而同去炒作绯闻!甚至连绯闻也没有,就自编一段并自我爆炒一番!

熊希龄故居内一角
熊希龄当年可是有一段实实在在不大不小的风流韵事的,而且还有“△”之嫌。
而立之年的毛彦文,从美国学成回国,才貌双全,是一位十足的江南名媛。同样才貌双全的北大名教授吴宓,为了她毅然抛妻弃子,正向毛发动着猛烈的爱情的进攻。而当时已年过花甲的熊希龄,竟然最终击败了吴宓,以六十一岁的年龄与三十三岁的毛彦文终成眷属,让吴宓一壶老醋一喝几十年,直喝到死。时人有联曰:
老夫六六,新妻三三,老夫新妻九十九;
白发双双,红颜对对,白发红颜眉齐眉。
那是一段怎么样风流,我们不难想象!或许这段并非是虚构的风流,的确为熊希龄被历史记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若说这是唯一原因,随着我越来越走近熊希龄,越觉得这太有失公道,因为有一个道理很简单,这个世界上每一天都有许许多多的风流韵事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但毕竟真能成为历史的并不多,为什么熊希龄的风流韵事能成为历史呢?
——这本身又成了一个问题。
二
历史学家们归纳一个人被历史记住的原因,总是或现民族大义,或益江山社稷,或建千秋功业,或留不朽杰作;当然,亦或相反,或罪大恶极,或祸国殃民。这样的归纳当然不错,但这样的归纳因为剔去了历史人物的血肉,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及其人生抽象成了几个概念间的推断,这常常会让人总觉得不太可信。我们是凡人,也是俗人,我们更希望知道某个历史人物,长得多高多胖,他(她)是不是也与我们一样有七情六欲,小时候是不是也尿炕,发起火是不是也骂娘,脚气发作了是不是也抠脚丫,伤风感冒了是不是也挖鼻孔…………
因此,我参观一些名人故居时,常常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与周边的百姓聊一聊,因为他们往往能告诉我一些有关这个名人的穿开裆裤时的一些事情,……而这些一定是高悬于祠堂式故居里的“生平事迹介绍”之类中所绝对没有的,而这些在我看来反而更接近名人作为一个人的真实面目。
当导游不遗余力地向游客添油加醋地讲解熊希龄六十一岁时与三十三岁的江南名媛毛彦文恋爱结婚的风流韵事时,我则在门口的一旁与一个打草鞋的老者攀谈了起来,并听到了另外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说,熊希龄出生的那天晚上,凤凰城里满街都清香扑鼻,人们由此断定这孩子将来一定是个朝中清官。还有人们听到这婴儿的啼哭声特别响,街邻们都说,这孩子哭声大,长大必成大器。
第二个故事是说,在熊希龄中举的第二年,逢花朝之日(阴历二月十二日,被当地认为是花的节日),当地知府朱其懿邀集官吏和新科举人在府衙内赏花,知府提议吟诗作画。于是济济名士,各显身手,有的画牡丹,题曰“富贵风流”,有的画荷花,题曰“出污泥而不染”,有的画菊,题“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虽然个个切题,但也均不脱俗套。惟有熊希龄则画了一株棉花,旁观者都大摇其头,因为中国画史上,向来少有以棉花入画的。棉花为农家所亲,怎能登大雅之堂?但只见熊不动声色,画完后于留白处挥毫题写了七个字:“此君一出天下暖”。这七个字真如画龙点睛,当即震动全场。熊希龄借棉花言志,不仅使自己名声大噪,还意外收获了一桩美好姻缘:朱知府赏识他的才华,作主将自己的五妹朱其慧嫁给了熊希龄。
虽然,这两个故事是从熊希龄的邻人嘴里讲出的,但我这一次却很怀疑它的真实性,因为太巧了——熊希龄晚年致力于慈善事业,无疑是到处“送温暖”。据有关资料显示,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只要哪里有灾,就会有熊希龄的出现;只要哪里有灾,人们也就会想到熊希龄。湖南是熊希龄的家乡,湖南省府当局,但凡发生了大灾,首先考虑到的便是向熊希龄求助,熊希龄总能够帮助解决问题,渡过难关。他真是“霖雨苍生”式的人物,这四个字是他逝世后湖南省政府对他的赞语,似乎正应了这个故事中熊希龄的这幅画和这句诗。因此,我怀疑,这个故事原本就是好事者,想要表现熊希龄的不非凡,而根据他的这一段人生,倒过头去附会出的故事。不过,如果真是这样,倒是历史以另一种方式对他的记录与肯定。不是吗?有时候,也正是这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故事,它们虽然扰乱了历史学家介绍历史人物的标准语言,为历史学家们所不屑,但是历史人物倒反而在这些故事中显得真切而生动,他们远比在泛黄的史册中更真实可亲。至少是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是这样。

鳞次栉比的凤凰古城
三
不可否认,在很长一个阶段,历史似乎已忘记了熊希龄这个名字连同与这个名字所代表的那个人。我读书时,无论是中小学历史课本中,还是大学历史教科书中,都很少提及他,以至于今天一般人根本连他的名字也没听说过,更别说对他有所了解了。
也不可否认,今天在中国文化坐标中的凤凰是属于沈从文的。自从沈从文写出了《边城》后,小说中那座如诗如画的边城在世人的心目中就是凤凰,凤凰就是那座边城!她既属于文学,也属于沈从文了。
然而我在与凤凰的普通百姓的攀谈中发现,他们似乎更在乎的老乡是熊希龄而不是沈从文,似乎熊希龄更值得他们骄傲和自豪,在他们的话语中,甚至觉得沈从文成了文学家有点阴错阳差。“沈从文没读过几年书!熊希龄才是文曲星下凡,是‘湖南神童”,他19岁就中秀才,21岁中举,24岁中进士、点翰林。”眼前这位天天以编织草鞋为生的老者,竟然对这位百年前的街坊的简历如数家珍。仅凭这一点,我觉得故乡凤凰倒真是没有忘记自己的这个乡亲熊希龄。其中的原因,我想不能否认有中国几千年来的官本位思想在起作用。在一般人看来,再著名的作家终究还是一介书生,一介书生怎能与一内阁总理相比呵,那可是相当于宰相!
但是,我又想,如果熊希龄一生就按部就班,按照那个时代多数读书人所梦昧以求的“读书—科举—做官”这样的人生三部曲走完一生,哪怕他最终也能官居宰相,那么,他这位百年后的街坊还会如此对他的简历如数家珍吗?人们还如此记得他吗?
这让我想起了那年去闻喜县礼元镇裴柏村参观的情景。去以前,我们据旅游小册子上介绍,便知道了此村历史上曾先后出过宰相59人,此村因此而被称为中国“宰相村”。但是,等到我们参观了此村,跟着导游从一座又一座“相府”进进出出了一通后,似乎头脑中还是只有一个数字而已,那一个个当年一定是炙手可热的名字,在我们的感觉中还是那么的空洞——事实上也没能记住几个名字。至于这些名字所代表的他们,又有谁知道他们中,谁长得高,谁长得矮;谁长得胖,谁长得瘦;谁有什么喜好,谁有什么恶习;谁喜欢吃辣,谁喜欢吃咸……我们都一无所知,因为历史并没能记住。
而熊希龄幸运地被历史记住了,但他的被历史记住,绝不仅仅是因为他做过内阁总理。
被历史记住的熊希龄,首先是一个维新人物。
然而熊希龄成为维新人物实在有点偶然。
1895年,熊希龄终于完成了他“读书—科举—做官”的人生三部曲,作为新科进士,官授翰林院庶吉士,春风得意于京城。而也就是这一年,陈宝箴任湖南巡抚,这位新巡抚大人不是别人,而是熊希龄的凤凰同乡。这位同乡前学,几乎是看着熊希龄长大,自然十分了解熊希龄的才华。此时他正力主“新政”,在湖南开学堂,办报馆,兴实业,正需要得力帮手,便很自然地想到了自己的这位小老乡,于是他便力邀熊希龄回湖南主持“新政”。1897年,熊希龄回到湖南,在长沙任时务学堂总理,主持校务。在这期间,熊希龄请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唐才常襄助,时务学堂一时成为新派人士荟萃之地。在舆论先行的基础上,湖南的教育、行政、实业,都有了新的气象,一时间内全国闻名,成为全国“新政”的一个重镇,与京城内康有为等人掀起的“变法维新”思潮遥相呼应。
而对于熊希龄来说,正是从这一段“新政”经历开始,便越来越偏离他原来设定的人生道路了。
1898年8月,也许是看重熊希龄在湖南新政中的作为,光绪帝电令陈宝箴,并要其传知熊希龄、江标等人,要其“迅速入京,预备召见”。(《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3,第538页。)于是,熊希龄与江标等相约,决定迅速同行进京,准备与先他们一步而去的同乡、同事梁启超、谭嗣同等一起,将正当如火如荼的“戊戌变法”推向深入。谁知正要启程之际,熊希龄突然病倒,且一病不起,进京之行不得不暂搁浅;而9月,慈禧太后便因戊戌变法而发动戊戌政变,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随即血洒菜市口。因病而未如期到京的熊希龄倒因此而逃过一劫;不过慈禧太后没有忘记他,下了一道严旨,“熊希龄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这一切,发生得不能不说实在是有些偶然。
但历史学家更多关注的是历史的必然,在他们眼里,那些偶然中难以发掘历史发展的规律。在他们看来,熊希龄的这场“大病”生得太恰是时候了,因此,他们竟然找出了发生这种偶然的种种必然:当时的湖南维新派人物,存在左、中、右三派,左派是谭嗣同、唐才常、樊锥和易鼐等,他们在与顽固派斗争中立场坚定;右派是陈宝箴和江标等,他们一旦受到攻击,便妥协调和;而熊希龄与梁启超则为中间派,中间派在与顽固派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是一副左右摇摆、畏缩规避的态度,而熊希龄的“生病”正是此态度的一种表现。
这是标准的属于历史学家的一种分析,但历史学家多“事后诸葛亮”。的确,他们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无非是谭嗣同、樊锥和易鼐曾在《湘报》上发表过大量主张维新的过激的文章和言论,尤其是最后谭嗣同还杀身成仁了,而熊希龄并没发表过太多明确主张维新的文章,尤其是最后还因“病”而活下了。我不是历史学家,我无法用更高明的分析来否定他们的这种分析,我也没有足够的理由证明熊希龄当时的生病是真是假,但是我想提醒的一点是,事实永远要比任何再高明的历史学家的分析要复杂:谭嗣同、樊锥和易鼐是曾在《湘报》上发表过大量主张维新的过激言论和文章,但是发表他们这些言论和文章的《湘报》社社长和主编正是熊希龄,而熊希龄的这一职务又正是陈宝箴所任命的。因此,他们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存在这种所谓的左中右三派,真很难说。至于说被杀的人就一定是坚决的维新派,活着的便是动摇派,那也太过简单。
在被杀的“戊戌六君子”中,有一个叫康广仁的,是康有为的亲弟弟。其实他与乃兄在政见上素无多少相同之处,平时康广仁就常常奉劝乃兄“不要惹祸”。康广仁的被捕和被杀,完全是因为康有为跑了而揪住他来当替罪羊和替死鬼。为此他在狱中急得以头撞地,啼哭不已。因此,对于变法维新他实际上是一个既谈不上赞成也谈不上反对的人,他成了“戊戌六君子”之一实在只是个屈死鬼而已。他的死不是偶然又是什么?若说其中一定有什么必然的原因,最多也就是因为他是康有为的弟弟。熊希龄是没能与谭嗣同一道为维新杀身成仁,但也因此而说他就是动摇的中间派,似乎也太过草率。作为一个生命的人的复杂程度,有时候也不比一段历史简单。
熊希龄的第二次政治辉煌无疑是他出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但是历史记住作为内阁总理的熊希龄的同时,更记得了一个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而终无可奈何的傀儡。
其实,熊希龄当上这个所谓的“内阁总理”也有点偶然。
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后,几乎对他事先对革命党人所作出的承诺全都食言,一心想恢复专制,孙中山等国民党(同盟会已改组成国民党)人不得不发动“二次革命”。这种情况下,在袁世凯看来,国民党自然是不能让它来组阁的;复辟的步子也不能走得太快,得找一个几方都能接受的温和派人物来组阁。他选中了熊希龄。
熊希龄是国会中第二大党进步党的党员,熊希龄组阁自然可以获得进步党的支持;可熊希龄并不是进步党主要的党魁,袁世凯觉得他在进步党中不会有太大的力量,这有利于对他的控制;而此时的国民党虽然仍是国会中的第一大政党,可是已经是有名无实,发生不了大作用,在国民党议员看来,进步党的内阁比军阀内阁好些,再加上南北战争还在进行中,国民党最主要的事情还是这个。因此,国会投票表决熊希龄为内阁总理,对于熊希龄来说自然是有点阴错阳差,但却自然非常顺利地获得通过了。民国二年7月31日袁世凯正式任命熊希龄为国务总理。
如果说熊希龄当上这内阁总理有点偶然,那么其命运则是必然。
熊希龄就职后,宣称要吸呐“第一流的人才”、组成“第一流的内阁”,但是事实上这由得了他吗?谁能入阁关键还得袁世凯说了算!因此,熊希龄这个内阁总理,实际上只是袁世凯的一个傀儡。这样,到民国3年2月,熊希龄便坚持辞去了总理一职。想来熊希龄这总理当得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么风光,对此时人曾作一联:
似遇而实未遇;
有为而终无为。
假如熊希龄的人生到此为止,那么这副对联无异是对他虽官至总理,看似风光,而实质无奈而平庸表现的最好概括。而历史最容易忽视的是平庸,对于两极,总是不会忽视的。这大概也是曹操为什么要说他“不流芳百世,便遗臭万年”的原因吧。至此,熊希龄的人生中实在还没有什么“流芳百世”的东西,倒是有两点,虽够不上“遗臭万年”,但也不能不说是他人生中的两处瑕疵:先后在袁世凯签署的解散国民党、解散议会的命令上副署。至此,我完全可以说,假如熊希龄的人生到此为止,历史是绝不会记得他的,即使有幸不会被历史的烟尘完全淹没,能留下一个模糊的影子,那这个影子也一定不会十分光彩。
历史终究还是记住了熊希龄。毛泽东曾评价熊希龄说:“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周恩来总理也曾说:“熊希龄是袁世凯时代第一流人才,是内阁总理。熊希龄的事,我看后就记得很清楚。”两位共产党的领袖人物都一致给予熊希龄这么高的评价,可见熊希龄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还是十分光彩的。
四
“烂漫之极复归平淡”,这似乎是人生的一种必然。
不必说熊希龄那两度走向“烂漫”多少走向得有点偶然——反正既曾有过烂漫,一朝走向平淡至少也不算是一种偶然了吧!
熊希龄的光彩人生恰恰是在他完全退去了政治光环、人生复归平淡后创造的。
中国人的平淡人生大体上有两种,最常见的一种是这样:购地数顷,建房数间,如果当官时攒的钱多一点,还会筑一座园林,就此住将进去,或纵情丝竹,或依红偎翠,享受生命,也放纵生命——那些精致的苏州园林多数当初的筑成原由和功用大体上便是如此。对于这样的人生选择,中国的历史,历来都是十分宽容的,有时甚至可以说还十分赞赏和推崇,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所谓“世人皆醉我独醒”,所谓“出污泥而不染”,皆是赞赏与推崇之现成之语。我想熊希龄完全可以选择这样的“平淡”方式,因为他除做过内阁总理不算,毕竟做过多年的财政总长,一定也曾攒下了几个钱。
至于第二种,人们更是推崇和赞扬,如陶渊明,用手中的笔写出传之后世的不朽诗篇。选择这样的“平淡”方式,我想熊希龄也应该是有条件和资格的,因为他早年不是就有“湖南神童”的美誉了吗!他不是早就吟出过被传诵一时的“此君一出天下暖”的名句吗?
然而熊希龄最终既没有选择成为又一个陶渊明,也没有为自己购地、建房、筑园等,相反,他千金散尽,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充满了艰辛、坎坷还常与误解、屈辱相伴的不归路。
1917年京畿一带发生大水,熊希龄积极参与救灾工作,并就此走上了一条以社会救助和慈善教育为业的艰辛道路。1918年,他创办了驰名一时的北京香山慈幼院,不但救助了数以千计的孤苦儿童,而且通过教育使他们成为对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之才。1924年,他又组织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并担任会长12年之久,不但在全国各地救灾办赈,而且还努力从事国际赈灾活动。熊希龄把自己后半生全部的精力和财力都无私地贡献给了这个世界和这个社会,使他最终不但成为了近代中国从事慈善的时间最长、贡献最大、知名度最高的慈善家,而且成了饮誉世界的大慈善家。
不仅如此,熊希龄作为一位慈善家,还有两点是一般的慈善家所难以企及的。
一是其高尚的民族气节中爱憎分明的民族立场。在许多人的想象中,慈善家虽然多值得尊敬,但往往多是些一派慈眉善目,开口闭口“阿弥陀佛”,有时甚至还有点糊涂,糊涂得无善无恶,敌我不分。然而熊希龄则不然。1931年,为了更进一步表明自己奔赴国难、矢志于社会慈善的决心和意愿,他在北京香山北辛村的熊家墓园自筑“生圹”,明示天下——自己一旦在抗日救亡中上前线救护伤病员时不幸倒下,即埋葬在这里;并自撰墓志铭:“今当国难,巢覆榱崩,若不舍己,何以救群?誓身许国,遑计死生,或裹马革,即瘗此茔,随队而化,了此尘因,我不我执,轮回不轮。”(见《熊希龄集》下册,第2087页。)其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献身救国的大无畏精神跃然纸上。
二是其从事慈善事业几乎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程度。1932年10月15日,熊希龄将自己的全部家产都捐献出来,计大洋27万5千2百余元,白银6.2万两,此为他从清末到民国为官25年的全部积蓄,他用这些钱在北京、天津、湖南三地,次第开办12项社会救助和慈善教育事业。当时熊希龄一家,夫人朱其慧已去世,还有一儿两女,但他没有留给儿女一点财产,而是悉数献给了社会救助与慈善教育事业。
这些不能不让人感动!尤其当我来到凤凰,走进了熊希龄故居,看见作为一代内阁总理,府上如此朴素的情形,这种夹着震惊的感动更是情不自禁。当然,我也似乎因此而明白了,为什么熊希龄在主动退出了历史舞台后,历史却终没有忘记他的真正原因。
1937年12月,熊希龄因北平沦陷而赴香港。就在到达香港当月的25日,因闻民国首都南京沦陷悲愤难当,而引起心脏病突发,溘然长逝,终年67岁。
至此,历史已不能不记住他!
当然,我说的历史并非是那些自以为是的历史学家所写的文字,也并非是那些多从实用主义出发而编成的教科书,而是存在于天地之间和人们良心之上的一本大书;因为历史若是前者,它常常是不公平的;若是后者,它总是公平的。因此,我有时更愿意相信人们口口相传的那些故事和传说,它们其实就是一个人留在世上的口碑,口碑中的东西往往比石碑上所刻的更真实,当然也更不朽。
我这篇文章写到这里就可结束了,突然想到熊希龄的那封信札——我那位朋友是不是还好好保存着呢?记得我当时看见它时只被它那漂亮的字迹吸引住了,究竟写的什么内容反倒没细看,于是很想再看一看。我拨通了我那位朋友的电话,朋友告诉我,那信札他一直好好保存着,曾经有好几个收藏家出高价收买,他都没有卖;他还告诉我,他家里还有一张熊希龄的照片哩。我急忙跑过去看,终于看清楚了那封信的内容。
原来我朋友的祖父为响应熊希龄赈救活动,曾捐出了一笔数目不小的款,为了答谢,熊希龄给我朋友的祖父写了这封信,并寄赠了照片一张。于是这信与照片在我朋友家里留存到了今天。
我也看到了那张照片,背面还有熊希龄的亲笔签名,虽然纸色已经泛黄,但好在仍非常完整,人物形象也非常清晰。照片中的熊希龄看上去五六十岁的样子,微胖,留着一把山羊胡子,正微笑地目视着前方,那微笑绝不是那种为照相而强作出的,是一种从内心自然流露出的笑,淡然、怡然、超然,那目光虽然并不凌厉,但似乎有一种穿越世俗,看破红尘的力量;眉宇间一派坦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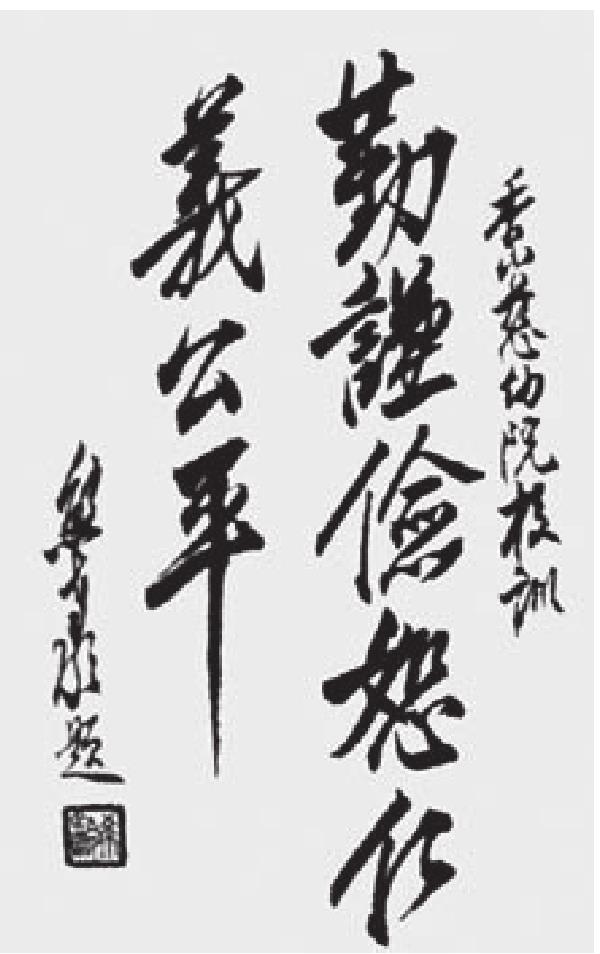
熊希龄亲笔题写的香山慈幼院校训

熊希龄
呵,我想像中熊希龄正是这个样子!
200/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