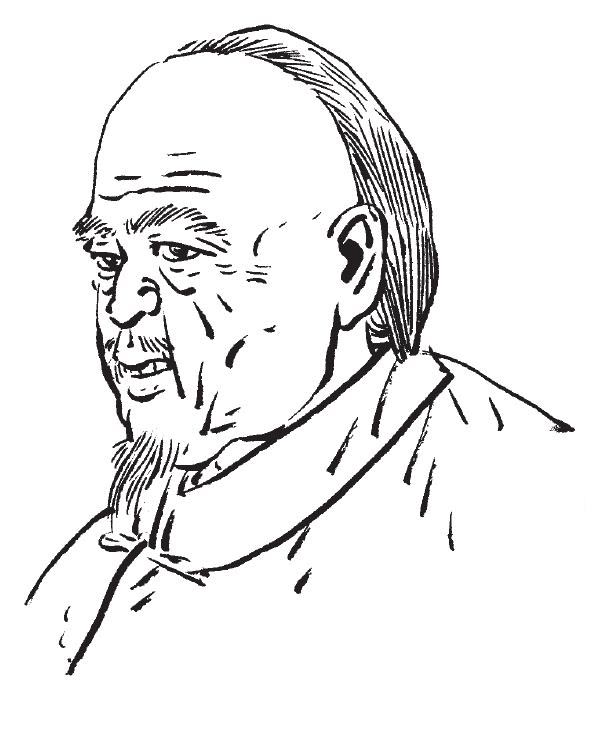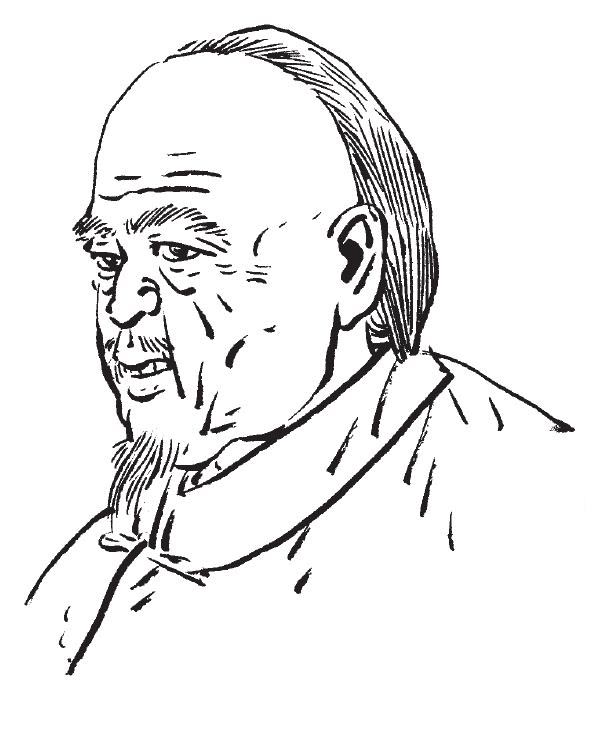
一
毓朗,字月华,号余痴,是敏亲王之后,是清末著名的王公贵胄之一。
毓朗生于咸丰四年(1854)。幼年的毓朗体弱多病,一直到20岁之前,基本上是足不出户。在清寂、森严的深宅大院里,这位小王爷倒没怎么觉得寂寞。他有一嗜好,就是读书,一天到晚手不释卷,确实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在当时,旗人重武轻文,王公子弟多以马步弓刀相标榜,毓朗嗜书如命,很不同于一般。他的父亲定慎郡王溥煦也很成全他,把家中几代攒下来的藏书都交给了他,任他翻阅。
毓朗不喜欢武事,但也免不了要习武射箭,这是清朝入关以来就给旗人定下的规矩。毓朗开始练习骑马时,已有17岁。当时他的兄妹都嘲笑他,说他甭说是马,连蛤蟆也是不敢骑的。毓朗蹩了一口气,翻身上马,疾驰而出。练马场路径崎岖,怪石嶙峋,毓朗脸上毫无惧色。等毓朗安然无恙地回来,兄妹都大吃一惊,深服他的勇气。
光绪五年(1878),毓朗24岁。这一年他参加武举考试中举,受封为镇国将军。与毓朗同时中举的还有善耆。善耆后来和毓朗同为清末重臣,对毓朗影响甚大。
毓朗中举,却没有被委以公务,他整天还是深居家中,以读书赋诗为乐。
这时候,已是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创痛。国家多难,旗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就连毓朗这样的王公之家也开始典卖古玩字画维持生计。但毓朗对这些似乎浑然不觉,他依然沉浸在他的书卷中,倒也悠然自得。后来,父亲溥煦为他谋到了神机营的小差事,毓朗推脱不过,开始上任。
神机营是皇室的禁卫军,虽然刚建立不到30年,但早已露出腐败之色。毓朗空有一身学识才情,在这里却得不到施展,他每天落落寡欢,很少和人打交道。当时,神机营的总办是岳柱臣,岳柱臣对毓朗没有什么好感,但知道他是贵族子弟,也不敢怎样怠慢。只是每次保荐人才,都没有毓朗的份。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了,神机营有一委员余仁建议编练龟蛋阵以御敌兵。按余仁的设计,是让士兵背负藤甲,匍匐至敌人身侧,然后以石灰迷住敌人的眼睛将之杀掉。余仁说,如果采纳他的建议,清军可稳操胜券。余仁提出这一建议时,很多人都为之心动,但毓朗鄙夷而嘲弄之,余仁非常狼狈。这里,我们应该交代的是,毓朗虽生于豪门深院之中,但他却接受了那个时代全新的思想,他所读之书多是西方器艺之书,和愚昧守旧的顽固分子大不相同。余仁本是市井无赖,因贩卖鸦片发迹,谋得了神机营的差事。他这时提出龟蛋阵这一不伦不类的“计策”,其实是为了谋得晋身之阶而已,见毓朗当众驳斥他,心中恼怒,发恨要报复。后来,毓朗见在神机营的确没什么出路,而余仁一类小人又百般为难,于是辞去职务回家去了。
光绪二十七年(1900),义和团运动兴起。五月,团民进入北京城,毓朗因素习声火电化等西方学术被指为“二毛子”,险遭杀身之祸。于是一家老小离京逃往郊区,躲避战乱。在京郊一个名叫三家村的山庄里,毓朗父子纠集了当地地主武装镇压义和团,打杀团民无数。
六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当时毓朗一家离京尚不太远,远远地看见北京方向火光冲天,大骇。在三家村,有人建议购置旧炮,以镇慑敌兵,溥煦很是动心,就喊来子女商议,毓朗坚决反对,下面这段对话颇能说明他的心机,也很能说明他的见识:
“购炮的意思,是为了向团民示威,可团民都知道那是废弃不用的旧炮,只能是白白示弱罢了; 现在八国联军已占领京城,他们听说有一个王爷固守一山,置炮八座,聚兵若干,是会发兵来打,这不是自惹事端吗?”
溥煦很不以为然: “你实在是太多虑了。”
毓朗接着说: “我们山中财货缺乏,以这有限的经费花在百天一用的大炮上,实在是划不来呀。”
溥煦还是听从了毓朗的意见。后来,其他村寨购置大炮,果然为侵略军所灭,溥煦深服毓朗的眼光。
究其一生,毓朗也算得上是精明强干,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却一错再错。他镇压义和团,是其地主阶级的本性使然,他在民族战争中畏首畏尾,不战而逃,只能说明他所出身的阶级正在坠落。
光绪二十八年(1901),清政府见大势已去,派庆亲王奕劻与侵略军议和,在签订丧权辱国的《辛日条约》后,北京的局势开始稳定下来,毓朗一家迁回北京。
经过八国联军的侵略战争,北京城千疮百孔,一片狼藉。定慎王府在战争中被法军占据,作了法军的指挥部。毓朗一家不能回府,于是租东成安伯胡同住下,聊以度日。
毓朗没有想到,就是在这个小胡同里,他的一生发生了重大转机。
二
在毓朗的后半生中,肃亲王善耆是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
就在毓朗一家在安伯胡同住下后不几天,另一位年轻的王公也搬了进来,这个人就是善耆。善耆是铁帽子王豪格之后,小有才气而不拘形迹,在当时颇负维新之名。22年前,善耆和毓朗一起中举,同投镇国将军,也算有着同门之谊。现在战乱初定,两个旧日相识聚到一起,自然是欣喜万分,以此谈诗论文,倒也颇有些情趣。
一天夜里,毓朗正在读书,忽然有家人慌慌张张跑来,说后院有人拆毁院墙,制止不听。毓朗连忙跑去观看,却看见善耆大笑着,正从墙那边跑过来。毓朗一问才知,原来是善耆觉得隔巷不便,毁墙为门以利往来。毓朗苦笑不得。
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慈禧逃往西安,善耆也曾跟随同往。现在他回到京城,其实是有命在身,慈禧授以他崇文门监督职,令他掌理税务。但在当时,北京正被列强占领,善耆根本无从任事。到第二年一月七日,慈禧回京,“中外合好”的局面已经形成,善耆这才走马上任。
善耆没有忘掉老朋友,他就任税务监督,也把毓朗带到了税署,后来善耆忙于他事,便索性将全部事物交于毓朗,让他总理其事。
以前毓朗或居闲职,或在家索居,从来没有管理过实际事务,现在他接受税务,不仅业务生疏,而且时逢中国新政,战乱初定,各种关系错综复杂,他能胜任吗?家人都为他担心,但毓朗回答得很干脆: “我这一生,有什么事是作不来的吗?”很快赴职。
确实,按毓朗的性格,不务事则已,一干就要干出个样子来,从此他早出晚归,一心扑在税署里。有一次善耆前来视事,看着毓朗瘦弱的身影跑来跑去,心中不忍,于是相劝: “署里事务繁杂,你能吃得消吗?”毓朗回答: “我既然接手任事,自然要尽心尽力,哪里还顾得上其他呢?”善耆深为感动。
崇文门税务在嘉庆年间就交给胥吏掌管,一百多年来百弊丛生。现在毓朗等人接手,改以西方资产阶级的税务管理办法治理,却又赶上大乱初定,一切都得另起炉灶。当时,和毓朗一同任职的还有陆宗舆(就是那个在五四运动中被罢免的三个卖国贼之一)等人,这些人因为善耆素负维新之名,投靠在了他的门下。他们在当时都很年轻,血气方刚又学有专长,正是精忠务事的年纪。崇文门税务在他们管理下,没出多久已是初具规模。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清政府的政策发生逆转,慈禧太后由镇压维新变法的刽子手一转脸变成了新政的“领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场全面的改革运动。崇文门税务还是这一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它起步早,而且卓有成效,很受慈禧的重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时至清末,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清贵族早已腐朽没落,他们文不能提笔为文,武不能领军作战,已成社会寄生虫的代名词。毓朗等人能在这种背景上脱颖而出,无疑给江河日下的满清统治注入了一线生机,他们也因此获得了“少壮派贵族”的美称。
当然了,在清政府内外交困的环境中,税务管理也自有它的难题,尤其是在西方势力已深入内地,清政府又在八国联军之役中新败的情况下。有一德国商人祁罗弗打着供应使馆的幌子,公然抗税,以前的税署对他只好听之任之。毓朗入署后,果断地决定扣留祁罗弗的货物,祁罗弗大怒,抬出使馆相讹诈,毓朗淡淡一笑,置之不理。祁罗弗果然从使馆拿来照会,他威胁毓朗说: 如果不为他的货物放行,将有重起战争的危险。当时正是外强气焰嚣张之时,没有人敢开罪于洋人,但毓朗自知公理在胸,对大使馆同样不买账。他不但不为祁罗弗放行,而且以扰乱公务,加倍征罚金。这下祁罗弗没了办法,乖乖地纳税了事。
正当毓朗在税署干得津津有味之际,善耆已考虑为他另谋差事。在战争中,日本侵略者控制了北京的警务,由侵略分子川岛浪速总理其事。根据《辛丑条约》规定,战后警权由清政府收回,但在当时,警务是中国从未有过的新事物,而且现在警权操在日本人手中,接手这一差事困难很大。清政府考虑再三,决定由善耆组建工巡局,负责接收警务。当时正赶上川岛浪速回国述职,善耆于是派毓朗与他同行,到日本考察警察制度。
从鸦片战争以来,清统治者就对中国以外的世界充满了或鄙夷或畏惧,或实有其据或荒诞诡秘的想象,到这时,终于有一位王公贵胄能走出国门,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个究竟了,这无论如何,都可称得上是一大进步。
三
毓朗起程前往日本,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五月十一日,在此后的两个多月中,他除了考察日本警务外,最值得一论的就是他同日本总理大臣桂太郎的相见了,这次相见对毓朗此后影响颇大。
八月初三日,毓朗等会见总理大臣桂太郎,他是毓朗在日本见到的第一个政界要人。
桂太郎一见毓朗,出语惊人: “将军知道我就是当年的义和团吗?”
毓朗一惊,忙问其故,桂太郎说: “我年轻的时候,也痛恨西方势力的东来。有一次我持刀潜上一艘美国舰艇,准备手刃一二美军,但我失败了,被美军抓住差点送命。从此我开始醒悟,靠蛮拼是无济于事的,于是潜心向学,遍游欧美。后来明治维新,我就依靠这所得新知,得以为国效力。”
一席话,说得毓朗大有茅塞顿开之感。
桂太郎接着谈到中国的情况: “日本派员出洋,其时是在中国之后,就像我这样愚笨之人,朝廷都能信用倍加,中国为什么就任学成归国之留学生投置闲散,不用他们为国效力呢?”
毓朗的回答不无诚意,却也不无为清廷掩丑之嫌。他说:“我们国家地大人众,按比例算,人才尚不足贵国十分之一,所以收效较迟些。现在国家推行新政,风气大开,我们将广招诚实务实之士,非以前可比也。”
桂太郎淡淡一笑,说: “将军知道吗? 现在地球正在缩小,各国间休戚相关,现在着手改革,已有为时过晚之嫌,将军请自勉之。”
毓朗深服桂太郎的识见阅历, 再三感谢后,才离开总理府。
日本在19世纪中叶时,本来和中国一样都是处于没落王朝的统治下,都是非常落后的封建国家,但日本在1868年以后,在全国推行了一场资本主义改革运动,从而一跃而成为亚洲强国,和西方外强不相上下,清政府有感于日本的巨变,在国内人民的压力下开始效法日本,这便是毓朗这次日本之行的背景。
毓朗东来之初,便抱定了虚心向学的想法,以求变法之道。事实上,他在日本确也开了眼界,长了见识,尤其是在参观考察中,他已基本上形成了他一整套的警务计划,这将对他回国后的工作带来直接的效果。
七月二十二日,毓朗回到中国。一上岸他便得知,善耆已保荐他为五品候补京堂职,让他出任警务总监。
毓朗日本之行,为他多了一番经历,也增加了一段新的资历,这在一个以改革相标榜的社会中,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四
现在人们一提警察,一般认为是始于1905年的巡警部,其实中国现代警察制度从工巡局建立时就开始了,时间应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
在警察制度建立的过程中,毓朗功莫大焉。
毓朗从日本归来,即入工巡局担任总监。当时,警权是掌握在“顾问”川岛浪速手中,虽然有《辛丑条约》的规定,他还是死死抓住不放。现在毓朗到任,他是不会容许权力操在日本人之手的。于是便有了下面一段颇富戏剧性的夺权斗争。
毓朗首先按现代警察制度对工巡局进行整顿,这也是他计划的一部分: 提高专业警事人员待遇,实行高薪金制,拉开和非警校毕业人员的差距; 提高警员地位,改变旧衙门中的恶习,待之以礼。
这两项规定渐次实行,就堵住了川岛浪速拒不交权的口实。然后,毓朗前往川岛浪速府邸,面商这事。
两人在过去混得相当熟,所以这次见面非常随便。
毓朗开门见山: “川岛君是一君子也,以后警务学堂之事,你操持就是,品德教育事关大事,地方行政之权,就由我管,这样可以统一事权,有事也便于指挥。消防队是从众人中选拔组建的,品格学问都好,就由你我共同管理。”
这时的毓朗正30多岁,言语自信而洒脱,且颇含机锋。
川岛浪速说: “将军所言很是,但中国官场多腐败,警署如不注重公务,那将作如何处理?”
毓朗笑道: “以前工巡局是别人任事,我们不好说什么,以后有我承担,或功或罪都义不容辞,日本之行,我们相处日久,阁下不信任我吗?”
川岛浪速无奈,只好应允。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有一次川岛浪速有事同毓朗相商,谈话中忽然话题一转,说: “我与将军相处日久,对将军颇为相信,只是把警权交与了你,人们都说是我受了愚弄,将军如何看法?”
毓朗大笑, “人言是不可信的, 阁下你觉得我能骗你吗?”
川岛浪速沉吟良久,说: “将军没有骗我,是我多虑了。”
川岛浪速能交出警权,其实这里是深有背景的。首先,国内反帝斗争虽经义和团运动的挫折,但这时却以新的形式,更加炽热地发展起来。而且,《辛丑条约》已规定了交接事宜,川岛浪速违约不交,不仅引起国人愤慨,列强对日本也开始不满。日本这时正在中国的东北同俄国激烈争夺,它不敢再在北京惹起事端,所以乖乖地交出了警权。
毓朗上任伊始,便根据他在日本考察所得以及早年居家时掌握的知识,拟定出庞大的警务治理计划。当时,有人拿来上海的租界管理章程,建议毓朗采用租界警事法,毓朗不准。又有人建议毓朗将警权范围扩大,推广到北京城区,毓朗还是不同意。在这两件事上,毓朗的想法还是很有道理的,租界章程管理租界则可,如果移到北京,物是人非,断不会有什么效果。现在北京内城警务刚刚建立起来,虽然已初具现代规模,但离巩固成形还相距甚远,如果推广到外城,和外城陈旧混乱的制度搅在一起,不仅不能有什么好的结果,内城中刚刚取得的成果也有断送的危险。
毓朗处事稳健,眼光又远,这里可见一斑。
毓朗上任后的第一仗,便是对民愤最大的赌风大开杀戒。
他封闭赌局若干,其中也包括宗室贵族的赌局。崇子后自恃皇亲,开起了赌局,和毓朗唱对台戏。毓朗知道这事,亲自带人前去查处,崇子后大惊之下,找到善耆疏通。毓朗对善耆也不买账,到底是将崇子后缉拿归案。
处理了崇子后,不仅为新建警务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毓朗也因此名声大噪。
毓朗管理工巡局,可谓达到了他一生事业的顶峰。虽然以后他还有升迁,甚至位列军机,但那时他已处于宫廷斗争的漩涡中,是明显的力不从心了。
在清王朝最后的10年中,颇有一些年轻的贵族忧时愤世,试图挽救这个正在走向毁灭的王朝。他们也曾努力过,也曾在自己的范围内干得有声有色,但在这个庞大的官僚机器面前,他们又实在是太微弱了。一个王朝在迅速地崩溃,单靠几个人的支撑已是根本无济于事了。
就在毓朗大力整肃赌风之际,各王府的赌局照常营业,其中以大公主府最为招摇,毓朗也只好听之任之。
光绪二十九年(1903),毓朗处理高尚仁聚赌案得罪了权臣奕劻,这一事件更成为他一生事业的转折点。他从此失势,而且再也没有振作过。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商人高尚仁聚众赌博,毓朗派人前去缉捕,在缉捕过程中,高尚仁将巡捕殴伤,毓朗于是将他带到了工巡局。事情发展到这里,一切都很正常。但在当天夜里,突然有庆王府人持文书来见毓朗,毓朗打开一看,原来是奕劻的一封信,说高尚仁和他素有交往,要毓朗放人。当时的毓朗年轻气盛,他不便直斥来人,就把一团怒气都发泄在了高尚仁身上,他告诉来人: “这是奸徒冒名之惯用伎俩,根本瞒不了我。”命人将尚仁带至公堂,掷文书于地: “你殴打巡警之事,明日讯明再说,今天就为这份文书惩治你。”命杖高尚仁40棍。送信之人在旁看着,无计可施。
毓朗痛责高尚仁,怒气渐平,但他很快又感到了后怕; 当时的奕劻权倾朝野,他能饶过我吗?
毓朗的想法不是杞人忧天,在那封建王朝中,开罪于权臣,确实也该掂量掂量了。
五
当我们回首百年前那场天翻地覆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我们容易简单地归因于革命者的经营和发动。当然,孙中山等人的功绩不可磨灭,但我们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反动阵营内部的斗争以至分裂,这是革命的背景,也是它成功的条件之一。
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从很早就开始了,到最后10年间,已基本上形成了两大派。这两派针锋相对,大有水火不容之势,而毓朗就卷入了这两派的争斗,并成为其中一派的主要骨干。
这两派中,一派以庆亲王奕劻为代表,外结袁世凯,内受慈禧太后的器重,是实力最大的一派。另一派以载沣兄弟为首,起初是因反对奕劻大权独揽而聚集到一起,后来由于善耆、良弼等少壮贵族的加入而具有了某种革新倾向。这一派中,虽然载沣也曾入值军机处,但势力相对要弱小,是正在发展中的一派。
从个人观念来看,毓朗倾向于载沣。现在毓朗和奕劻发生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派别斗争的结果。
1903年工巡局的变动是巨大的,正巧这一年善耆因丁母忧辞职,奕劻奏明慈禧,把大学士那桐安在了总监位上。
那桐是满洲人,依附于奕劻,两个狼狈为奸,以贪财好利颇得骂名,时人称他们为: “庆那公司”。那桐的到来也带来了他的一批私人,工巡局发审处等重要机构都被他们占据。
那桐等人属于旧派官僚,同按现代观念建立起来的工巡局是格格不入的。他们的到来使工巡局重新回到原来腐败、混乱的境地里,尤其是发审处,以贪赃枉法、草菅人命为能事,已成为恐怖、罪恶的代称。
毓朗虽然留在了工巡局,但处处受到那桐等人的压制、打击,郁郁不得志。同时,他又眼见着自己多年经营的成果被这些人糟蹋殆尽,实在是很痛心,万般无奈之下,他决定离开工巡局,转而向其他方面以求发展。
正巧,当时学部尚书张百熙正筹划新学堂,“教育救国”的呼声也早已出笼,教育界似乎还有所作为,毓朗于是去找张百熙。以前,毓朗东游日本,张百熙曾托他物色理化专长的人才,毓朗推荐了佐伯信太郎,很得张百熙满意。现在毓朗以一个王公贵族想筹办教育,张百熙自然是求之不得。于是,两人决定,由毓朗负责筹建觉罗中学堂一所、小学堂四所,立即开始准备。从纠纷中刚刚脱身出来的毓朗又充满了激情,他开始为建校事宜四处奔波。然而,这次毓朗却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他空有雄心,现实的条件却一个也跟不上。由于经费的缺短,世俗的讥评,也由于毓朗实在缺乏教育方面的才识与经验,建学堂的计划流产了,毓朗也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教育部。
光绪三十年(1904)初,毓朗到鸿胪寺任少卿。第二年的三月,再升为光禄寺卿,很快又升为内阁学士。毓朗的这几次升迁,都是得力于载沣一派的提拔。这时的慈禧太后已感到奕劻等人的权势过大,特意擢升载沣一派以相互牵制,毓朗的升迁就是慈禧这一想法的一个直接结果。然而,到这时,清政府已是日薄西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虽然新政的倡议几经强调,但慈禧本来就三心二意,言不由衷,而且,一个没落的王朝已是病入膏肓,积重难返,结果便是雷声大、雨点小,新政措施见效甚微。能够有所起色的部门,如毓朗之工巡局,也因各种原因而夭折。在这种败落萧条的情况下,本来就拟裁撤的鸿胪寺、光禄寺变得更为冷清,毓朗在职其间也就无所事事,除和善耆等闲聊外,毓朗又重新拾起书卷,以期度过这萧条的岁月。
六
光绪三十一年(1905),毓朗以内阁学士授巡警部左侍郎。以前那桐总监工巡局,局务一片混乱,终于酿出革命党人吴樾炸出洋五大臣的事来。清政府为自身安全计,决定组建专部,以徐世昌为尚书,毓朗和赵秉钧为左右侍郎,加强警政。
巡警部初建时,有人建议以武职划分官阶,毓朗坚决反对。用他的话说: “武弁已经久为社会所轻侮,武职官阶也早已流于卑鄙龌龊,一旦以武职命名,组建警部的原意顿失,已经风气大开的警政也就因此断送了。”毓朗的见解很有见地,后来巡警部建立,设立文官职,果然同以前面貌不同。
在巡警部,虽然徐世昌对他很尊重,也很信任,但毓朗却一直是愤愤难平。这气愤倒不是来自个人成见,而是源于那根深蒂固的满汉观念。在满汉观念上,毓朗属于死硬派。以前管理工巡局,他曾几次拒绝招汉人入局,他认为,工巡局之设是为了给落魄的旗人谋条生路,汉人是没有资格染指的。而现在,汉人不但进入了警察系统,而且徐世昌还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他自然是怨气冲天。而且,也还不仅是观念上的问题,徐世昌是袁世凯的亲信,这在当时已是尽人皆知。综观天下,军事大权已基本上掌握在了袁世凯手中,现在他又插手警务,这无疑是逼着清王朝向死亡再走一步,他能不忧虑,不愤慨吗?
毓朗时刻想着把权力夺回自己手中,然而,他失败了。徐世昌何许人也?单看他在民国时期无一兵一卒却能操纵各派军阀于股掌之上,就可见其心机权谋,毓朗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何况他背后还有袁世凯,还有那个只管贪财自肥,不问清政府生死存亡的奕劻?毓朗即使再急,也是无计可施。
光绪三十二年(1906)八月,定慎郡王溥煦去世,毓朗袭贝勒。按清朝定制; 贝勒不能兼二品以下职,于是毓朗辞巡警部左侍郎,朝廷以御前行走开其缺,其实是将他再度升迁。
毓朗离开巡警局了,其实也是他自认在同徐世昌斗争中的失败。这时的他只能眼见着清王朝这驾战车迅速地坠落下去,他也束手无策了。
光绪三十三年(1907),毓朗被任命为步军统领。步军统领的职权和巡警部基本相似,掌管守护京师和缉查事务。不过,这一职务非亲信是不能担任了,载沣把毓朗安在这一位置上用意还是很明显的,他希望毓朗能在这里重起炉灶,与徐世昌抗衡。
毓朗走马上任了,但时隔不久,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清朝统治者内部发生了一次大变动、大改组,整个的统治局面也为之一新。
慈禧是在1908年的11月辞世的,临死前,她选载沣的儿子溥仪入继大统。载沣父以子贵,受封为摄政王,势力大增。
载沣一上台,立即发动强大攻势,向奕劻、袁世凯等人发动了进攻。这一系列的行动以将袁世凯黜退回籍开其端,继而任用他的弟弟载涛编练禁卫军1200人,他的另一个弟弟载洵掌理海军,自己则出任海陆军大元帅。
形势的变化也为毓朗带来了利益,载沣命他到编练处任大臣,和贵族中对军事颇有心得的铁良、良弼等负责编练禁卫军,以强化同袁世凯抗衡的资本。
然而,虽然机会有了,但毓朗的身体条件却坏了下来。他早年即体弱多病,这时已是50多岁,体力已渐有不支之感。在编练处,他也只能看着铁良、良弼这两个年轻人忙里忙外,自己已是力不从心了。
宣统三年(1911),毓朗身体有所好转,正巧,这时清政府改军咨处为军咨府,作为陆军的参谋机关,毓朗和载涛被任命为军咨府大臣。
在这一系列升迁中,表面上看毓朗是飞黄腾达,大权在握了,其实不然,他在频繁的升迁后,依然是郁郁不得志。这不得志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他同党中更为年轻的那批人。
或许是我们对政治斗争中感情因素的作用太忽视了,我们在理解这段分歧、不和时,感到了些许的困难。在禁卫军编练处,为什么勇于任事的良弼会对同样以作风凌厉著称的毓朗越来越不满?在军咨政府,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是载沣的弟弟,一个是载沣的宠人,载涛和毓朗也是矛盾重重,这是为什么?仅仅是因为毓朗老了,迟钝了,甚至有点愚蠢了?或许,并没有那么复杂,只是性格的差异罢了,从能得到的资料看,毓朗是孤僻的、阴郁、葸缩而又拘泥刻板,一句话,他不是那种受社会欢迎的性格,即使是今天也是如此。
在清政府灭亡前的这段时间里,毓朗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唯一值得一记的是,他曾奏请建立了贵胄政法学堂,并出任总监。他的意图还是很明显的: 为清廷培养现代行政人才。但时间已不允许他,政法学堂建立还不到一年,清政府就被革命的洪流推翻了。他的这一“政绩”也只能随之流逝。
七
毓朗一生中担任的最高职务是军机大臣,时间是在宣统二年(1910)七月。
对毓朗的这一任命充满了荒诞气氛。
毓朗接受任命后的第二天上朝当值,正碰上政敌奕劻和那桐,二人脸上颇有异色。毓朗似乎感到要有什么事发生了。中午时候,隆裕太后召摄政王载沣晋见,载沣进去后,却好久不见出来,庆、那二人脸上颇有得意之色,又过了一会,一章京出来报告说载沣已回府,奕劻忙问是否有太后谕旨下,章京回答说没有。奕劻就很不解: “怎么会没有呢?怎么会没有呢?”
其实,毓朗能入军机处都是载沣之功,庆、那二人非常不满; 甚至隆裕太后也被二人说动,颇有罢黜之意。那天中午,载沣晋见就是为的毓朗的去留问题。当隆裕太后提出罢免时,载沣知道是庆、那二人所为,很生气。他要求过几天再讨论这事,想以此敷衍过去。但隆裕太后不依不饶,载沣被逼得没办法,以后宫不能干预朝中大事为由,隆裕太后才不说什么。
毓朗的军机大臣一职是保住了,但他从此便被排除在军国大事以外,根本不能参与决策。以后,军机处四人每次上朝,都是点个卯即刻退下,然后奕劻、那桐、载沣三人再被召回,这才开始讨论朝政。
九月间,资政院成立了。资产阶级立宪派集聚其间,向清政府展开了强大的和平攻势。资政院第一次会议时,曾邀请奕劻到命答辞,奕劻不肯。后来邀请再三,于是四大臣公推毓朗前往。毓朗自知这是奕劻等人排挤他,但守着那个处境尴尬的军机大臣一职也实在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他答应了。
在资政院,面对群情激奋,唇剑舌枪的议员,毓朗倒显得镇定、机警。下面就是答辩词:
有议员问: “朝廷对于速开国会是否赞成?”
毓朗答: “朝廷已有旨,很快即会召开御前会议,此事将取决于公意。”
有议员问: “军机大臣所负责任如何!”
毓朗答: “关于此事,已接到贵院质问书,日内即有复文到院,这时我不便口头答复。”
有议员问: “军机大臣是否赞成速开国会?”
毓朗答: “庆王等人是否赞成,非我所知; 如果非让我回答,我敢肯定地说,现在已决无反对之人。”
有议员再问: “贵大臣是否赞成,抑或反对?”
毓朗答: “国会是否宜于速开,本大臣自然已熟虑于心,只是不日即有御前会议召开,我这时不便先说什么,以免嫌疑。”
……
如此唇剑舌枪,相持二时许。
议员所提问题,无一不事关当前政治中的热点问题,但毓朗还是在几乎不能回避的时候回避过去了。第二天的《国民公报》报道此事说: “昨天朗大军机到院,举止安详,神情镇定,胸中似了了者。然出言滑脱,按之殊无实际。”——确是入木三分。
宣统三年(1911)三月,清政府抵挡不住立宪派的压力和革命派日益高涨的呼声,宣布取消军机处,成立新内阁。新内阁由奕劻任总理,那桐和徐世昌副之。本来,清政府设新内阁的原意在于作作表面文章,以消弥革命,而事实上,新内阁却操纵在皇族手中,成为皇族集权的一个重大步骤,这便无疑是给这个早已空气紧张,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的火药桶投下了一点火星。
8月,传来北洋将领张绍曾在滦州发动兵谏的消息,要清政府交出政权,否则将发兵北京;
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的怒火迅速传向四方,清政府已走上穷途末路;
同月,清政府万般无奈之下起用袁世凯镇压革命,国内局势顿时变得奇诡莫测;袁世凯在与革命党人达成协议后,进京面宫,虽然有善耆等王公反对,清政府灭亡的命运已不可避免,隆裕太后挥泪签署让位诏书,统治中国200多年的王朝结束了。
……
当这一切发生时,毓朗差不多是一无所知,军机处取消后,他也就自然而然地离开了军机大臣的位子,回家赋闲去了。12月13日,即让位诏书签署的第二天,他才得知巨变的消息,悲愤之下去找川岛浪速商议,但终因得不到皇室的音信而放弃。
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随之开始,无论愿意与否,毓朗必须面对这一现实。
八
辛亥革命后,毓朗在北京作起了寓公。
离开政坛了,他重新回到他的书斋。在他的一生中,书是太重要了。书曾给他教益、眼界,现在则又给了他失意后的寄托,给了他晚年的安乐。
1915年,正是袁世凯帝制自为紧锣密鼓的时候,毓朗因形势的恶化,决定东渡日本,然而日本使馆的领事却劝阻了他。领事认为,如果他东渡,袁世凯一定怀疑是王室或前清大臣的阴谋,那将对王族非常不利,毓朗考察再三,放弃了这一想法。
这时的毓朗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他突然之间患上了脑病,虽经德国名医施密得的精心治理,但也没有怎么明显的效果。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任总统,下令在全国进行议会选举。这时的毓朗病情稍有好转,于是他上书部院,为满族争取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满族作为清王朝的统治民族被推翻了,但它毕竟是民国所宣布的“五族”之一,冯国璋不能不接受毓朗的建议。后来选举结果揭晓,毓朗和庄王溥绪当选为参议院议员。
清朝倒台后,毓朗的那些故交挚友,如善耆、铁良之类,大多走上了反对民国的道路,为清王朝的复辟奔走呼号。毓朗能到民国任职,可谓一大进步。
毓朗任议员后,身体状况时好时坏,任内基本上没什么作为。1902年,直皖战争爆发,参议两院因涉嫌支持内战受到指责,毓朗索性离职,回家养病去了。
民国初年的政坛错综复杂,风云变幻,但毓朗已不可能参与了。历史的浪潮滚滚向前,毓朗为之服务的清王朝灭亡了,他自己也在这历史的起伏中,被淹灭、被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