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廖逸农回忆,因共舞台案涉案人数众多,审问次数频繁,普遍审问2次,另有1次大对质审问。李植先从调查科叫来告密叛徒李典,又名唐桂生(冯桂生),问明部分情节,由李典指出案内李逢春(即李鸿春)、王灿、李文达关押在上海时,三人就已动摇。李逢春供出了中共江苏省委地址,因此捕到了肖万才。后来李植利用李逢春、王灿、李文达,叫他们暗中刺探,秘密提出报告,还利用相互牵扯、个别指正等阴险手法,查清一些人的案情、身份。同时,季源溥也布置了一些在押的叛徒暗中刺探。但是直至结案,敌人都始终没有弄清全案的主要负责人。审问两个月(应该是一个半月)后,进行了判决。
实际上,判决前,军法课已确定了原则。即突出两个重点:一是确认这次大会是非法的,二是强调当场围捕。这样,对于搞清组织身份的人可以按其身份定判;对于没有搞清身份的人,既是出席非法集会的代表又是当场被捕的,也就可认此定判。总之,只要到了军法课,就是最后的阶段了。
廖逸农说,判决结果是:死刑13人;判各类徒刑者60多人;交家属领回管教的青年学生8人,他们大都是事先有人向陈立夫说过情了;交保释放的,仅有中年妇女肖郎氏1人,她双目失明,是肖万才的妻子;叛徒李逢春、王灿、李文达3人没有被判刑,由调查科提去留用,做了特务。在这些被判刑的“政治犯”中,最小的一位叫做张毛宝,当时他才十五六岁,是一个印刷店的学徒。
审问期间,调查科派出的主要干事之一季源溥经常前去参加,与法官李植商榷,共同进行,即为会办,也就是会同办理。季源溥并不参与军法课的审问,他每天主要是带去人员及叛徒。他进入看守所提审案内被捕者,骗取组织人事关系等。同时也帮着军法课搞清一些人员的真实身份,以利审判。在与季源溥的接触中,廖逸农听说这次案件是调查科事先获得了情报,并逮捕了有关人员,于是派出主要干事顾建中率人在上海布置破坏的。先是派出了大批人员,监视沪西某些公共场所,广泛侦察。当天,接到上海市警察总局督察处转据劳勃生路警察分局电话报告,知悉共舞台将开大会,经核实,乃由顾建中亲率人员及武装警察,乘伪装车辆掩护前往,才得以当场围捕。
季源溥当面告诉李植,围捕成功后,上海某些知名人士即出面说情,要求保释某几个被捕青年。上级认为这种情形非应付不可,于是写了几个名字给李植,叫他审讯时注意,以便将来保释。李植和廖逸农专办此案。在审问过程中,人数太多,审问频繁。绝大多数人只载明是“出席大会代表”。他们一头雾水,找不出重点,很多人身份不明。所以李植又与顾建中接洽,由顾派来“自新人”,即叛徒李典(唐桂生),及其妻唐王氏前来提供情况。
李典是在共舞台案前不久被捕的,他是中共沪西区委的成员。对于案内被捕人员,他知道李逢春是党员,与肖万才有组织关系,知道王灿为区委委员,并负责接待代表出席大会,同时他还指出李逢春与李文达等被捕后在上海时就已动摇,甚至肖万才的地址就是李逢春提供的,说这三人可提供较多的情况。后来,李植便提出李逢春与李典见面,让其“现身说法”劝李逢春“立功”,李逢春表示接受。随后就利用李逢春、王灿、李文达三人,让他们在看守所内对同案人员暗中刺探,提供“小报告”,即秘密报告,然后再利用其他方法获取组织身份。季源溥另外还布置了一名叫做李振东(应为李耀东),系其他事件中的叛徒,暗中侦查,提供“小报告”。这些报告,为审讯提供了便利。全案经过两次普审,一次大对质后,约在10月份开始结案。结案前,季源溥已事先和军法课主任贺伟峰商定了判决原则,最后由谷正伦商同陈立夫批定。
据温济泽回忆,1932年7月29日夜,他们被移送南京。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的院子,他们一个个被剃光了头,胸前挂上写着“赤匪”两个大字的纸牌子,挨个照相,并挨个在登记表上按指纹,先按十个手指纹,再按十个脚趾纹,然后换上更重的脚镣,被关进号子(即囚室)。每个号子里都架着双层床,上下通铺,两层紧挨着睡十几人。地上放一个马桶,没有多少可以走动的空间。8月的南京,正值酷暑,墙壁被太阳晒得发烫,号子里热得像个火炉。马桶臭汗,熏得人恶心欲吐,就连呼吸都感到困难。蚊蝇乱飞,臭虫乱爬,身上又黏黏的,更令人难以入眠。就这样,他们之后被敌人挨个审讯。
据龙潜回忆,他们被押到宪兵司令部看守所,这个看守所的两排房子前后都是警卫和看守。敌人不睡觉,他们一心想要破这个案子,从沪西搞来叛徒唐桂生(即李典),并押来了唐桂生出卖的肖万才夫妇(肖的女儿王小宝,儿子肖明山都是同案)。特务想从肖氏父女身上寻找突破口,但提审王小宝时,王小宝不承认肖万才是她的父亲,敌人只好作罢。提审时,唐桂生坐在法官李植的后面,一个一个地指认,认出来的点点头,认不出的摇摇头。很快,唐桂生认出了李文达、李鸿春、王灿、张德生,李文达和李鸿春被连夜提审,结果他们叛变了。接着王灿和张德生也叛变。
由唐桂生咬出李文达、李鸿春、王灿、张德生,再由他们指认出一些人,共舞台案便被定下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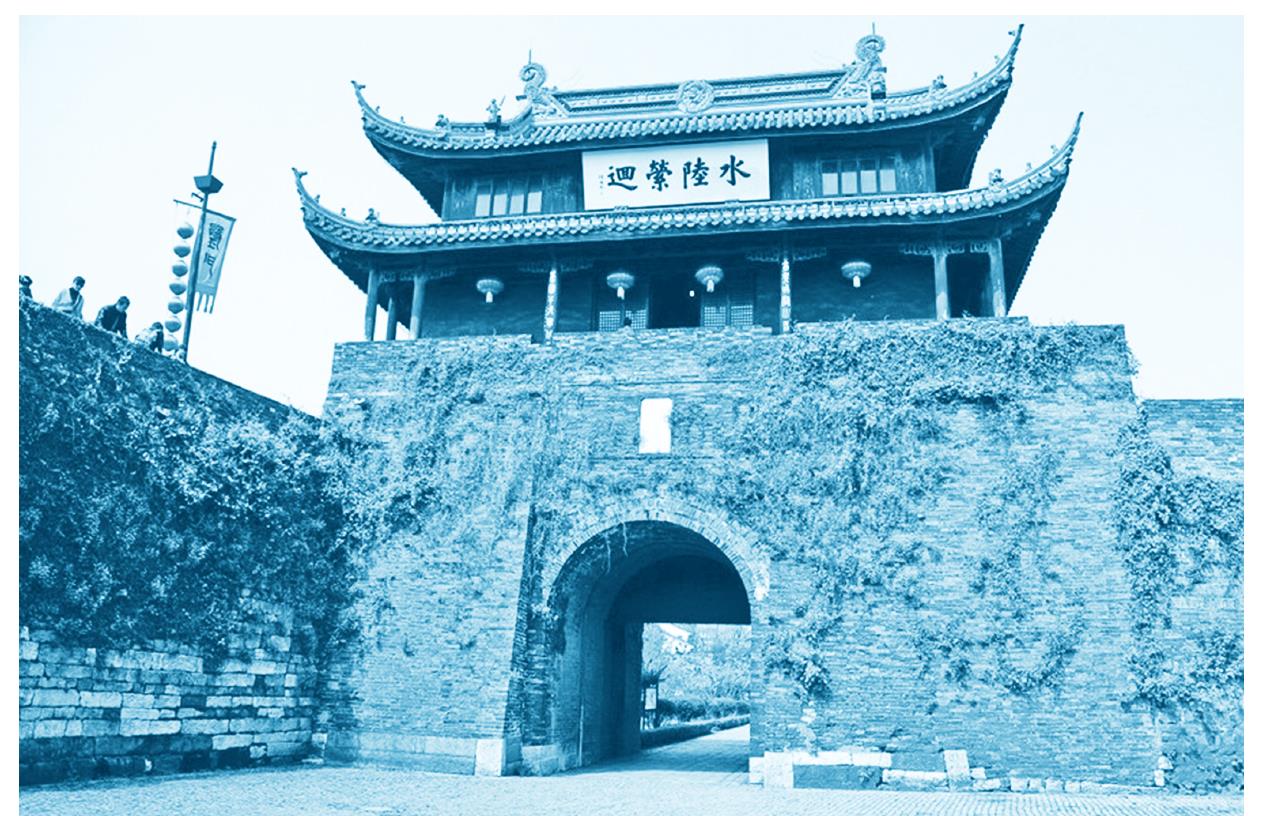
苏州盘门古城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gongwutai/2022113420.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
2023-02-15主编
2023-02-15主编
2023-02-15主编
2023-02-15主编
2023-02-15主编
2023-02-15主编
2023-02-15主编
2023-02-15主编
2023-02-15主编
2023-02-15主编
2022-11-29主编
2022-11-29主编
2022-11-23主编
2022-11-18主编
2022-12-08主编
2022-12-08主编
2022-12-02主编
2022-11-29主编
2022-11-29主编
2023-01-03主编
2022-12-04主编
2022-11-29主编
2023-01-24主编
2023-01-03主编
2023-01-24主编
2023-01-03主编
2022-12-06主编
2022-10-28主编
2022-12-02主编
2022-12-31主编
扫码二维码
获取最新动态
